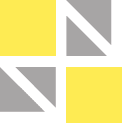色的通感:蔡宗隆和葉庭安雙個展
文 黃荷雅
「色」固然是一種視覺能見的客觀存在,然,在更多數的時間裡,「色」能打開我們的其官感,我們會說「慘白」,會說「黑壓壓」,也會說「鮮紅」,在顏色詞的前後加上綴詞,而這種綴詞便來自日常生活。試想為何白色是「慘」的?為何黑色令人感到「壓抑」?為何紅色是「鮮」的?錢鐘書先生說:「在日常經驗裏,視覺、聽覺、味覺、嗅覺、觸覺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,眼、耳、舌、鼻、身各個官能的領域可以不分界限。顏色似乎會有溫度,聲音似乎會有形象,冷暖似乎會有重量,氣味似乎會有體質。」
作為雙個展,蔡宗隆和葉庭安的作品能夠在同一個空間,透過「色」激迸出日常的花火,筆直地通向觀者的五感。「通感」其實是一種文學上常見的寫作技巧,上一段提及的例子便是如此,再補充說明,張愛玲便是將此技巧使用的爐火純青之人,像是《傾城之戀》:「她坐在床上,『 炎熱的黑暗』包著她像 葡萄紫』的絨毯子。」「黑暗」通向觸覺的「炎熱」,而「葡萄紫」也是一種視覺上的想像;像是〈年輕的時候〉:「學校裏搖起鈴來了。晴天上憑空掛下小小一串金色的鈴聲』 。」 「金色的」視覺通向聽覺的「鈴聲」。以上便是「通感」的說明,若要說這種寫作技巧能夠達到什麼具體的效果,我想便是「共感」。這一效果顯然是藝術鑑賞上不可或缺的一環,西方浪漫主義的其一核心亦圍繞在「理性」與「共感」之課題,以下將說明這二位藝術家如何以色使觀者共感。
在葉庭安的作品中,「色」的使用顯然被觀者注以好奇的眼光,一個畫面往往呈現數種不同的色彩,而作品名稱往往是一客觀的存在,我猜想或許生活中的各個色彩映在她的視網膜上,能夠折射出或輕盈、或混屯、或自由的色彩印象,而她以此自由鋪張,像是〈海浪〉一作中,以天藍色混著淡紫的色調,這顯然並非「海」會有的顏色,而她並未將海浪具體地描繪出「漸層」又或是「白色的浪花與藍色的海水」這種對照,或許我們可以試著遠觀其作,我赫然發現,她的作品如同一種「印象」(impression),模糊而朦朧,卻是由真真實實的畫面轉變而來的。因為是一種「印象」(impression),所以自然而然地結合了「其它印象」,因此海的顏色結合了浪漫的淡紫色,甚至可見一些草綠色、蓮藕粉點綴在旁,站在這樣的作品前,彷彿耳邊傳來陣陣浪花的拍打聲,鼻尖一動似乎有些鹹濕的海味,髮梢隨海風輕揚。另外,也有另一種創作脈絡,可見〈簡單點〉一作,「簡單點」好像並非是一個實體物品或存在,然而,我想或許她提煉了生活中所有能夠令她「簡單點」的顏色,不論這樣的顏色出自哪樣的物體,其實這也是一種「印象」(impression)的體現。除了顏色的運用外,葉庭安的筆觸更像是一種不間斷的實驗,有時刷,有時拍,有時又砌,這與她的自述「直覺、意外和驚喜是核心」相呼應。這樣的作品使我想起《獅子的點心》,雖未能直述到底聯想到處,然而或許是同樣的療癒之效,使得感官得到舒緩。如果說布列松強調的是一種「決定性的瞬間」(the decisive moment),我想,葉庭安傳達的便是一種既非瞬間也非永恆的,不含任何批判與預設的視角,或許這便是為何她的作品能夠以視覺的色通向其他感官的體驗之因。
蔡宗隆的「色」或許不及前者的繽紛,然,白、黑、青等色在中國早期被視為五色,與五行和五德相對,例如周朝奉「火德」,因此朝服皆為赤色,而這樣的傳統也間接影響色的文化意涵,例如,白色為西方之色,對應為金行和秋季,而我們又常以日薄西山比喻人之衰老,於是,白色被當作是送葬之色,而白色亦有「純潔」之意味,見《詩經》:「野有死麇,白茅包之;有女懷春,吉士誘之。林有樸樕,野有死鹿;白茅純束,有女如玉。」總而言之,我想說的是,葉庭安的色是一種源自於生活的發現、凝視而成的印象,而蔡宗隆的色便是潛意識繼承傳統,使觀者因其基因而共感的牽引。在〈朵2406〉一作中,以茶黑色為基礎,如同從黑色的礦石中見到翡翠的微光,蟹殼青的釉色從茶黑色中細細地冒出來,也如同在烏雲中不慎冒出的束束光源,彷彿乘著這片雲朵穿梭到遙遠的朝代,小橋流水,柳絮輕飄,一股清新的泥土味,戀人獨目成。〈向光〉系列,花草樹木褪去豔麗的外裳,米白色的胚土混著礦物沙,像是湘妃竹,也像是雨點滴答的痕跡。回到最原始的狀態和最原始的本能「向光」,體現出生之欲,觀者彷彿能聽見其吶喊,滿溢著活力地渴望陽光,我想,春天之鮮美,並非在於花朵之嬌豔與旖麗,而在於那源源不絕的生命力。蔡宗隆的作品中,色與形融為一體,動與靜渾然天成,而觀者能夠透過表淺的色通向感官的體驗,進而了解到形,甚至是作品的動靜態描述,蔡宗隆巧妙地編織出這樣一個緊密的網,觀者在網中懸掛、沈醉。
蔡宗隆與葉庭安的作品像是一真一幻;一是立體佇立的,一像是輕飄在夢境中;色的運用上則是一以最基礎的色牽引觀者五官,再撒下一張大網使觀者無法掙脫於作品中的生命力,另一則是以提煉生活的色彩,自成一抽象而真實的印象。於是觀者以眼觀,而後鼻、耳、口皆觀,情緒蕩然,與之相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