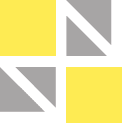人間散策—以生命哲學試析徐嘒壎藝術
文/謝佩霓
從而立之年晉入不惑之年的徐嘒壎,原本長年從事影像藝術,近年轉而投向平面繪畫。從掌著長鏡頭朝外看待周遭客體,選擇作為寧可置身事外的旁觀者,輾轉成為甘受任何悸動波及也不迴避的當事人,箇中的心路歷程微妙,著實耐人尋味。
徐嘒壎認為自己的攝影、錄像和平面繪畫,雖然都在以不同媒材套疊出視觸覺(tactile)來探討抽象的範疇,不過截然不同。她說影像的處理是以技術性的操控,設定預設值,達到預期的結果。繪畫則不然,從起心動念到停筆完成,每一刻都得在衝突間和自己奮力搏鬥。
根據作者自述,創作是她關於記憶的探索及內在生命的回應,帶著眷戀、模糊以及遠方氣息的這些元素,「用盡最精巧的力氣加密她的不安全感」。 若然,透過生命哲學按圖索驥,不啻是嘗試解讀徐嘒壎作品的可行之道。
這一派的宗師,非柏格森(Henri Bergson, 1859-1941)莫屬。
每當需要描述世界或者再現現實,柏格森寧可採用圖像和隱喻,也不願使用概念,畢竟概念有其偏頗武斷之處,往往無法觸及整體現實。經由分析及觀點來創造概念,好比從各個角度拍攝照片,建構出來的只是由抽象累加成的網絡,看似合理合度,卻未必合情通情。合理化的集體演化,加強的只是重複實踐的智能,卻無法取代奇思異想,反而足以賦予直觀推測帶來突破。也許這也是徐嘒壎暫別影像的原因之一。
世界由空間與時間組成固然成立,但兩者具備的本質可不一樣;空間具廣延性 (extensity),時間富綿延性(durationality)。從計時器通行以來,人誤解時間是個連續體,如同時鐘上指針位移或者數字增減,徹底忽視忘卻了時間是質變的載體。柏格森不以為然,時間雖然可以依附於均值的空間,藉由度量衡予以測量,看似可以科學理性分析,但實情是人心相對浮動,對時空的感受,時時刻刻都可能瞬間驟變,無必然性與規律性。因此追求性質的多樣性,遠比數量的多樣性要符合人性。
問題是長久以來,人們習慣以度量衡顯示的變化來理解空間與時間的關係,誤認駕馭以單位累進的自然科學時間,才能主宰了一切,忽略甚至再不相信,人心目中「真正」的時間,其實是生命時間。除非意識到概念的局限性,並具備直覺的絕對掌控能力,是無法參透為何天涯咫尺,芥子如何可以納須彌,光陰可以似箭,但度日也可能如年。
徐嘒壎畫不停手,展現了掌握瞬息萬變的企圖。不過她深知時間的純粹性,不是靠等分等值客觀累加獲得,而是容許不斷主觀的疊加參與,方能產生深刻豐富的多重意涵。唯有如此不斷扣問生命情境,探索內在自我,才能真正掌握生命更迭遞嬗的無窮變化。
誠然,有機生命的「持續時間」(durée)自有其極限無法延長,卻帶著異質性,不必然一模一樣。柏格森所謂的持續時間,遠非恆定不動,而是不斷移動、流動、恒動而永動。人唯有透過直接經驗來體驗,借助個人直覺才能理解之。亦即人必須放任自由意志直面事物本身,以自主且無可預測的方式展開,才能為因果騰出異度空間,創造嶄新結局的無限可能。
徐暳壎的努力,著墨於創造分享彼此記憶的共享空間。沒有記憶的能力,學習便無從發生,練習和複習,都是為了增強記憶。雖說記憶能化時間為生命力,但她同時以作品提醒我們,遺忘的能力對生存同樣關鍵。適時地選擇性遺忘,方便人即時定位,增強順天應時的適應力,不再執著於過去,能夠放眼未來,有助於個體與集體續存。
現實絕非一成不變,相反地完全是由改變組成。因此,看待身份多元的徐嘒壎一張張的畫,何妨視之為形形色色的「便利貼」(Post-It)。便利貼既是為了擇要記住當下的重點而存在,於每一個轉折點設定節點,更方便於隨時可以盤點、重新排序與重組記憶,形成貫穿過去現在未來的文脈。
相當自律的畫家徐嘒壎勤於筆耕,有如日日夜夜伏案的作家。事實上,每幅作品的標題,都像一句句現代詩,隨機一口氣讀來,足以構成ㄧ篇篇散文詩。不由得教筆者想起波蘭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朵卡萩(Olga Tokarczuk, 1962-)的創作手法。她善於系統性化整為零,透過縮影投射(vignettes)打破線性思考,利用多線發展挑戰閱讀慣性。一絲一縷毫不馬虎,逐步織出斑斕的大塊錦繡,朵卡萩以建構星系(constellation)自況,創作協助仰望星空的眾生,投射想像於繁複星宿為寄託。無獨有偶,金牛座的徐嘒壎亦復如此,前次個展她以「密室的畢宿五」挈題,就是好例子。
策展人段存真(1977-)認為,密室象徵藝術家內在的棲地,欲解其寓意,必須根據她提供的線索,辨識出相關座標,才能找到解鎖的鑰匙。筆者倒願意這麼想,徐嘒壎以沉浸式的藝術交感,築造成個人詩意的棲居,同時也貢獻出人人得以密室脫逃的完全攻略。一如此次展覽命題「我在找你然後你找到了我」所揭示,「找」和「我」之間,差別不過就在最關鍵的那第一筆。那一筆理應就是創造性的一筆。
柏格森在宇宙本體論的基礎上,認為生命衝動(impulse),才是論證從直覺到本能乃至於綿延的關鍵。他認為直接經驗和直覺的過程,比抽象理性主義和科學對於理解現實更重要,唯有對變化能有所感知,人才能獲得心靈能量。在永續人類繼起之生命的直覺催化下,唯有「創造性衝動」不斷,才足以令生命力源源不絕。肯定個體差異,否定整體重複,這是德勒茲(Gilles Deleuze,1925-1995)的忠告。處於精神分裂的世道中,如何打破演化論的制約,其實不是一味守成趨同,而是讓多樣併置勃發,才能永保生生不息。
已故希臘導演安哲羅普羅斯(Theo Angelopoulos,1935-2012)御用的電影配樂大師希臘作曲家卡蓮珠(Eleni Karaindrou 1941-)曾說,她感覺自己像個畫家,從千千萬萬種色彩中醞釀,選出作品的底色。她以細膩的音色沁入,創造了電影時刻,而創作靈感來源就是日常生活體驗。安哲羅普洛斯運鏡,講究以客觀角度呈現故事情節,交付觀眾思考,而卡蓮珠的音樂,善於激發人心隱匿至深的情感。徐嘒壎的創作,個人認為作品饒富音樂性,頗見異曲同工。
反覆觀看徐嘒壎繪畫和靜態攝影作品,不難發現依然可見嫻熟靈巧的變換「運鏡」。她既是影中人又是掌鏡人,容許自己被多重文本附身。有如化身悲傷草原中施然躑躅的那隻鸛鳥,日復一日清理生命榮枯興衰所遺留下的細碎,以虔誠之心蒐集這些時間之塵,視若珍寶並向我們獻寶。領略一砂一世界之美的我們,於是隨著她的節奏,欣然跳起了小步舞曲(minuet)與嬉遊曲(divertimento)。
言談舉止和她的工作室一樣有條理,但不難看出徐嘒壎到底是感性之人。藝術家非理性的自然而為,一經啟動便散發出無比的生命能量,而創作者內在生命哲學,便會隨著作品鋪陳生發落定,而自成格局定格。情不知其所起,却一往情深,她說永遠清楚幾時是該停筆的一刻,自是猶如行雲流水,於其所當行,戛然止於所當止。
生命動能的質量必須儲存足夠,才得以駕馭肉眼可見的美及五官可感的妙,而一但充分駕馭,就能悠遊自得酣暢得意而忘形。畫面融融自洽,細節豐滿沛然,瀰漫美的覺力。
畫布或大或小,端的適情適性,總歸皆是作者在操持生活中閃現的吉光片羽。看似輕如鴻毛,翻飛疊加之後,神奇地就把藏不住春色夏意秋光冬景,納為人間四季。
尤其當作品一字排開,沿著作者居住空間蜿蜒成風景線,逡巡穿梭其間,沐浴在照明下,產生了的別樣情緒。觀者明白,這絕不是鍛練繪畫體能的健走,甚至不是計畫型散步,而是即興但持之以恆的散策。
魏晉南北朝士大夫好服五石散修道,服後因須散熱而吃寒食兼散步,遂成「行散」。後來文人相約行散成風,一起回顧安步當車的漫遊生活,吟詩作對十分風雅。即使從此別過,兩相忘於江湖,也還有夢,而且像徐嘒壎一樣堅信「我們的夢彼此押韻」。
日人在大化革新時全盤接受唐風,散行從此也成為大和民族體悟生活奧義的散策。班雅明(Walter Benjamin,1892-1940)挪用波特萊爾 (Charles Baudelaire,1821-1867)描繪現代畫家的用詞,強化了藝術都市漫遊者的形象,徐嘒壎未嘗自外於列。不過相較於普魯斯特(Marcel Proust,1871-1922)筆下的女性角色,都是難以捉摸的行人(passantes),畫家徐嘒壎是個行者。
生為理性與感性兼備之人,徐嘒壎儘管堅持畫布規格必需遵循文公尺來訂製,透過六識的洞察力,在散策人生時,倒是頗能覺知常人錯過的蛛絲馬跡及可觀之處,然後懂得如何付諸畫筆墨,在畫幅中淋漓表達。
君不見是皂片(Soapfilm, 2016)剪影也好,是瑞斯特(Pipilotti Rist,1962-)的閱讀筆記也罷,每件創作都是心跡的集成,蘊含一個個含苞待放的花心(korfulamu)。
欲以時間切片阻擋時間高光流逝,看起來是癡心妄想。不過即使最後是徒勞,註定會留下美的足跡。知其不可依然為之,不也是何其浪漫?
展名 | 我在找你然後你找到了我 徐嘒壎個展
I was looking for you, then you found me. HuiHsuan Hsu Solo Exhibition
展期|2024/09/7(六) – 10/19(六)
開幕茶會暨藝術家座談|2024/09/28(六)15:00
與談人|謝佩霓